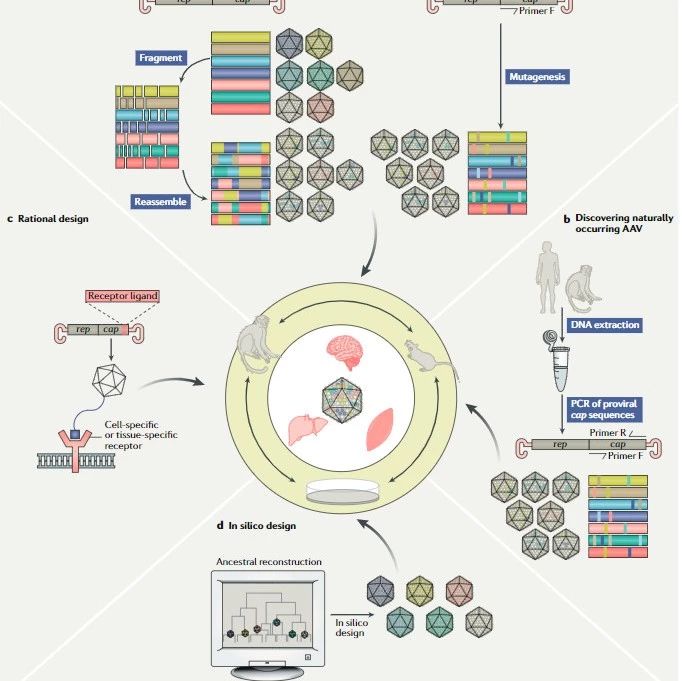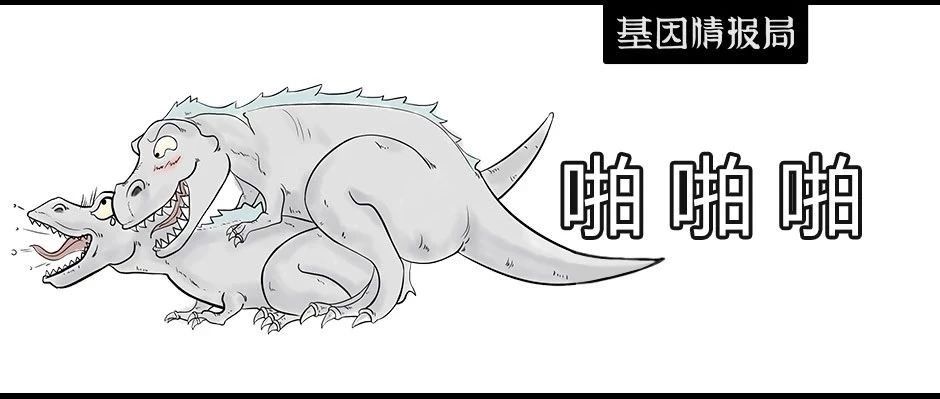基因与人种:人类的同一性与多样性(一、二)
人们对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看法也许有许多种,但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类型:从空间上看,生物之间的关系是直线式的还是分支式的?从时间上看,生物之间的关系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在西方,从亚里斯多德开始,采取的是一种最简单的、既是直线式又是静态的观念: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依次排列,组成了一个逐级上升的阶梯,位于最底层的是最低等的生物,位于最顶端的自然是所谓万物之灵的人了。这个“自然界的伟大链条”的观念影响极为深远,直到18世纪才开始受到冲击。林耐第一个打破了这个链条,把它改变成分支式的。当他把人归为哺乳动物纲灵长类下众多物种之一时,事实上已剥夺了人类在自然界中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但是,正如布封在反驳林耐这种分支式的归类法时所指出的,按照这种归类法,必然会推理出所有的动物都来自同一种祖先(而这种进化的观念在布封看来是错误的,因此林耐的分类也就是错误的),而林耐本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在林耐的宏图中,生物彼此之间并无亲缘关系,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之所以被归在一起,只是因为上帝在创生时对他们用了类似的设计蓝图,并非由于他们从共同祖先进化而来。对这种静态观的冲击有赖于比林耐稍晚的拉马克。然而拉马克的进化观却是直线式的,他不过是把“自然界的伟大链条”改成了动态,低等的动物在努力进化成高度的动物,高度的动物在努力进化成人,人乃是进化的目的和顶峰。正是达尔文对林耐和拉马克的观点进行了取长补短的扬弃,创建了分支式的进化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一个不断生长、分支的进化树上的一个支点,很难说哪个更高等。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从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的,是进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既非进化的目的,更不是进化的顶峰。
达尔文主义虽然早已成为生物学界的主流,但远远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许多人仍然象18世纪的林耐一样,拒不承认生物进化的事实,而那些接受进化的人当中,又大多抱着的是拉马克式的直线进化观。人类不过是进化的一个偶然的、并不比其他生物更高等的分支,这种观念,对普通读者而言,还是新颖甚至有点骇人听闻的。正确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是正确地认识人类自身的基础。
但是人类学的研究具有特殊性: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都是人,研究者往往已有了预设的社会观念,难以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因之难以避免因社会地位、经历而导致的社会偏见。当研究的是其他生物,例如小白鼠时,研究者有什么样的社会观念无关紧要,对研究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当人本身成为研究对象时,研究者的社会观念却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研究的结果,也可能被带上“科学”的客观性、权威性的面具,而被用于支持已有的社会偏见,甚至引发新的社会偏见。人类学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了社会偏见乃至悲剧的历史。
一、人种学的起源
当林耐把人归入分支式系统时,他遇到了一个问题:人这个物种是否应该再分支,分成几类?林耐当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给人分类的人,但却是第一个试图以“科学的方法”这么做的人。在《自然的系统》这本划时代的著作的第一版(1735年出版),林耐将人划入了灵长类,但并未对人做进一步的划分。从第二版(1740年出版)开始,他把人分成了四个地理亚种:红种的美洲人,白种的欧洲人,黄种的亚洲人和黑种的非洲人。这样的划分法似乎很顺理成章,合乎“常识”,直到今天,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人种大抵也是分成这四类。林耐对他鉴定的物种都有一个简单的描述。有必要仔细看一下林耐是如何描述人种的:
美洲亚种:红肤色,坏脾气,受抑制。头发黑、直、粗;鼻孔宽;脸粗糙,胡须少。顽固,易满足,散漫。身上涂抹红条。依照习惯统治。 欧洲亚种:白肤色,严肃,健壮。头发金黄、飘垂。眼睛蓝色。活泼,非常聪明,有创造力。穿紧身衣服。依照法律统治。 亚洲亚种:黄肤色,忧郁,贪婪。头发黑色。眼睛黑色。严厉,傲慢,充满欲望。穿宽松外套。依照舆论统治。 非洲亚种:黑肤色,冷漠,懒惰。头发卷曲。皮肤光滑。鼻子扁平。嘴唇厚。女性外阴下垂;乳房大。狡诈,迟钝,愚蠢。身上沫油。依照怪想统治。
按今天的标准,这样的描述显然属于以欧洲为中心的种族主义。但林耐很可能并非有意这么做。如果他有意确定欧洲亚种的优越地位,那么我们难以理解他为什么把美洲亚种而不是欧洲亚种排在最前面。这样的排列法表明,林耐试图不偏不倚地把四个人种当做自然界中地位平等的四个亚种,但是在做具体描述时,仍然无法摆脱当时流行的社会观念的影响。于是在他的笔下,不知不觉地根据其审美标准对欧洲人进行“美化”而对其他种族进行“丑化”,尽管只有少数欧洲人是金发碧眼,“金发碧眼”却成了欧洲亚种的特征,而欧洲人体毛较浓密这一“原始”特征就不提了。欧洲人当然最聪明,性格也最无可挑剔,其他人种要么愚蠢,要么让人讨厌。对社会制度的描述最能反映出当时的欧洲人对人种等级高低的看法:依照法律统治的欧洲人胜过依照舆论统治的亚洲人,后者又胜过依照习惯统治的美洲人,而最低级的当然是依照怪想统治的非洲人了。当林耐把性格、社会制度这些非自然的特征做为人类亚种的属性时,就已偏离了“自然的分类”。事实上,除了这四个地理亚种,林耐还根据道听途说为人类设了两个非自然的亚种:一个是“野亚种”,这是根据那些在森林中发现“野孩子”的报告而设立的;一个是“怪物亚种”,包括传说中的世界各地的种种怪人。显然,林耐并不是象对待其他生物那样对人类进行自然的划分,而是根据笼统的归纳、价值判断、社会偏见和传说来划分人类。
前面已经提到,布封做为林耐的对手,反对系统分类法。他在研究人类的多样性时,也不试图把人分成几大类群,而是从生理上和文化上描述了许多民族(中国人、日本人、爪哇人、爱斯基摩人、埃及人等等),尽管在描述时,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偏见。通过比较这些民族的异同,他试图确定他们之间的历史关系并解释他们是如何演变的。他用一个相当于现在所谓微进化的理论试图解释人类做为单一的物种,是如何从同一祖先演变成今天这么多样的分化的。他将导致人类分化的因素归为三种:气候、食物和奴隶制,后者是指将人从气候和食物最适合其生存的原住地强迫迁移到其他地方。布封并设想,气候对种族差异的影响是可以通过试验来验证的,比如可以将塞内加尔人迁到丹麦,不与当地人通婚,看看经过多长时间,丹麦的气候将会使他们的肤色变白。
可见,布封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采取的是与林耐截然不同的方法。林耐用的是分类法,而布封则用的是描述、分析、历史和实验的方法。他所问的问题不是人类可以分成几大类群,各大类群都有什么特征,而是人类具有怎样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都是怎么演变而来的。然而,虽然布封的著作在当时非常流行,被广泛阅读,但是他在学术界的声誉比不上林耐。虽然布封的方法更具有现代意义,但是在以后的两百年间,却是林耐的分类法被认为更为“科学”,而在学术界获得继承。
布鲁门巴哈一般被视为人类学的创始人。他在1775年向哥廷根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论人类的自然变异》,跟林耐一样,将人类分成了四个种族,但是对划分的范围和描述与林耐的并不完全相同。在该书的第二版(1781年出版),布鲁门巴哈给人类增加了一个种族,即马来人种,并对前四个种族的划分做了修正。这五个人种,分别被称做高加索变种(白色人种)、蒙古变种(黄色人种)、埃塞俄比亚变种(黑色人种)、亚美利坚变种(红色人种)和马来变种(棕色人种)。我们看看布鲁门巴哈又是怎么描述人种的:
高加索变种:白色肤色,粉红色面颊;毛发棕色或栗色;头半球形;脸圆而直,各部份轮廓略为分明,前额平滑,鼻狭窄,略呈钩状,嘴小。门齿垂直地分布于上下腭;嘴唇(特别是下嘴唇)有些张开,下颔圆满。
蒙古变种:黄色肤色;毛发黑、硬、直而稀疏;头近方形;脸宽,同时扁平和凹陷,各部份轮廓因此不分明,似乎要混在一起;眉间平坦且非常宽;鼻小,似猿;面颊常为球状,向外突出;眼睑开口狭窄,呈线状;下颔略微突出。
埃塞俄比亚变种:黑色肤色;毛发黑色而卷曲;头狭窄,两侧扁平;前额呈节状,不平;颊骨向外突出;眼睛非常凸出;鼻厚,看上去象是与宽阔的上下腭混在一起;齿槽狭窄,前端拉长;上门齿倾斜地凸出;嘴唇(特别是上嘴唇)非常饱满;下颔收缩;许多人为罗圈腿。
亚美利坚变种:铜色肤色;毛发黑、硬、直而稀疏;前额短;眼眶很深;鼻子有些似猿,但凸出;脸无例外地都是宽阔的,面颊凸出,但不扁平或凹陷;脸部各部份从侧面看时轮廓非常明显,就像是经过深度雕刻的;前额和脸的形状许多都经过人为的改变。
马来变种:棕色肤色;毛发黑、软、卷、厚,并且茂盛;头有些狭窄;前额略微肿大;鼻饱满,相当宽,就像扩展开来,尾端厚;嘴大,上腭有些凸出,脸的各部位从侧面看时,十分凸出而分明。
与他的老师林耐相比,布鲁门巴哈显然要客观得多。他不再用文化、性格特征来描述人种,而只限于解剖特征,用语也尽量平实,看上去更具有“科学性”。但是布鲁门巴哈的做法,却充满了矛盾:
他认识到所有的人类都属于同一个物种,人类的一个“变种”会与另一个混合,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划分变种将是主观的作法,然而他还是坚持把人类划成了四、五个变种。
他认识到人类的形态存在着连续的、复杂的变异,并不能做简单的、明确的归类,然而他觉得通过描述某些特殊的形态,就可以把他们当做人种的典型,而其他的形态都可做为这些典型的变异。
布鲁门巴哈可能是同时代的西方学者中最不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做为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有意识地反对种族主义,强调所有种族在生理、心理和智力上都是平等的,他特别否定那种把黑人视为劣等人的流行说法:“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特别的在埃塞俄比亚人当中普遍存在的特征,其特征在人类的其他变种中都可以观察到。”并确认“尼格罗人(黑人)的心理能力和天赋是完善的”。然而,布鲁门巴哈虽然避免了将性格、文化这些主观判断引入人类学研究,却毫不掩饰地将另一类主观判断──审美观做为研究的基础。他虽然极力强调所有人种在生理、心理和智力上的平等,却不认为他们在美学上是平等的。他如此解释为什么把一个包括欧洲、西亚、北非和爱斯基摩人在内的人种命名为高加索人:
“我以高加索山命名这个变种,是因为在这一带,特别是其南坡一带,产生了最美丽的人种,而且因为在这个地区,我们认为最有可能是人类的发源地。”
布鲁门巴哈认为“最美丽”的高加索变种乃是上帝最早创造的、在形态上最理想的人类原型,后来在不同气候和生活方式的作用下,虽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发生了退化,虽然在生理、心理和智力上保持等同,在外貌上却变得越来越丑陋,一条退化路线是从高加索变种退化成蒙古变种,亚美利坚变种是其过渡形态;另一条退化路线是从高加索变种退化成埃塞俄比亚变种,它也需要有一个过渡形态,于是马来变种就被制造了出来,林耐的四个地理亚种变成了五个人种。林耐至少在表面上承认各个人种在自然界的地位平等,而布鲁门巴哈却是公开地在人种之间划分自然等级,最高(最原始)的是高加索变种,其次是亚美利坚和马来变种,最次是蒙古和埃塞俄比亚变种。
现在,虽然已无人认为人类内部有亚种之分,但仍然有人类学家把人类分成四大基本种族。与林奈时代不同的是,美洲原居民被归入了亚洲人,另外多出了一个澳洲人。《剑桥人类进化百科全书》(1994年版)是这么描述这四个人种的:
高加索人:分布自北欧到北非和印度。皮肤色素有不同程度的消减。男性头部和身体的毛发普遍发达,并大多纤细,波状或直。以窄脸和突出的窄鼻子为典型。
尼格罗人:分布在非洲撒哈拉之下。皮肤色素浓密,头发卷曲,鼻子宽,脸一般较短,嘴唇厚,耳朵近似方形,无耳垂。身材变化大,从非常矮小到非常高都有。
蒙古罗人:分布在除了西部和南部以外的亚洲,北太平洋和东太平洋及美洲。肤色从棕色到白皙,毛发粗,波状或直,脸部和身体体毛稀少。脸宽并倾向于扁平。在中部群体眼皮被一个内部皮肤皱褶覆盖,但在其他地方该皱褶不明显或没有。牙齿经常有复杂的牙冠,上门齿内表面常为铲状。
澳大罗人:澳大利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原居民。肤色深,头发以波状或卷曲为主,儿童普遍为金发。头长而窄,有突出的眉脊和下颌。
这样的描述的确是非常客观的了,已丝毫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然而客观的描述未必就是客观的事实。虽然避免了林耐、布鲁门巴哈的种族主义偏见,却继承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无视人类形态变异的连续性,而根据某些特殊的形态将人类划分成少数类型。典型是本质,而个体变异并不重要,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在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即使在达尔文认识到每一个个体变异都可能是重要的,从而创建了群体思维之后一百多年,仍然有待改变。
二、人种学的罪恶
在达尔文看来,进化并没有方向,生存竞争的结果导致多样化,而不是进步。但是达尔文这个正确的观念,在当时以及以后一百多年间,都没有被普遍接受。人们仍然像拉马克时代一样,把“进化”当成向更高水平、更复杂程度的进步。一位叫做斯宾塞的达尔文同胞,不仅歪曲了达尔文学说,把自然选择当成生物进步的动力,而且把这种说法推广到了人类社会,让达尔文的名字与一种臭名昭著的社会学说——“社会达尔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斯宾塞看来,你死我活的竞争既是生物界,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使得人类进化成万物之灵,而通过社会竞争——例如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欧洲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掠夺——才使得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处于人类文明的颠峰。
做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言人,斯宾塞对人类社会的看法是乐观的,“进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但对没落的贵族阶层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却是人类社会正在退步的怨恨和恐惧。这种悲观情绪在经历了大革命的动荡的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贵族当中更为显著。在1853-1855年,一位叫戈宾诺(Joseph-Arthur Gobineau)的法国伯爵出了一部四卷本的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试图从人种学的角度为人类社会的退化——特别是“已在欧洲各国肆虐了这么多年的血腥战争、革命和无法无天”寻找依据。在研究了希腊、罗马和日耳曼民族的兴衰之后,戈宾诺确信种族问题盖过了其他历史问题,是解决其他历史问题的关键;组成一个民族的各个种族的不平等,足以解释这个民族的命运。戈宾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总共存在十种文化,每一种文化的兴起都是因为“亚利安人”给当地人民带去了高贵的血液、艺术和知识的天赋。按照这种说法,在世界各地都应该曾经存在过亚利安人,而戈宾诺也的确到处发现了亚利安人。随着亚利安人的血缘被稀释,人种即退化,而文明也就开始没落。文明创建者中亚利安血液的纯粹程度,决定了一个文明的兴衰。在这些高贵的血液被外来的元素稀释、冲淡,不再能发挥作用之后,文明也就必然灭亡。这样,在他看来,所有伟大文明的衰亡,并不是由于人们经常提及的那些腐败因素(“奢侈,政府管理不善,宗教狂热,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人种的退化。
戈宾诺对人类遗传的理解——血液的高贵、纯粹、稀释云云,与欧洲中世纪的迷信一脉相承。那种认为人类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天性的观念,也自古就有。戈宾诺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文明的兴衰归结为种族天性的不同和混合,而且最终追溯到单个种族——亚利安人。他把人类历史的进程简化成了遗传的演变,似乎为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客观基础。像戈宾诺这种既有“学术性”又简单明了,涵盖全世界、概括人类历史的气势恢弘的大理论,总不难找到追随者,何况是一个可以为社会偏见提供正当理由的学说。当戈宾诺鼓吹亚利安人是最美丽、优秀的人种,而“大洋州的人有幸提供了最丑陋、堕落和可恶的种族样本,似乎是被创造出来为了展示人和单纯的畜生之间的链环”时,他在当时的欧美社会找到了无数的知音,须知那是一个伟大如杰菲逊、林肯也相信白人和黑人是截然不同的种族,而前者的身体和心灵都比后者高等的社会(杰菲逊:“黑人不管是起初就是一个不同的种族,或是因时间和环境造成了不同,身心两方面的天赋都比白人低等。”林肯:“我相信白人种族和黑人种族之间的体质差异将禁止这两个种族能在社会和政治平等之下共同生活。既然他们不能共同生活,他们在一起时就必须有上等和下等之分,而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赞同把上等位置划归白人种族。”)。戈宾诺的著作很快就走出了国界,在西方世界找到了市场。1856年,一位鼓吹奴隶制的美国人就在费城出版了戈宾诺著作的英译本。英国的版本也随后出现。但戈宾诺最大的知音出现在德国。在作曲家瓦格纳的笔下,那个想象中的亚利安人被艺术化成了日耳曼民族的象征,成了他颂扬日耳曼文化、抵抗外来“污染”的工具。1899年,瓦格纳的英国裔女婿休斯顿·张伯伦(Houston StewartChamberlain)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建立于戈宾诺的理论之上的种族主义著作《十九世纪的基础》,影响重大。十几年后(1916年),另一部种族主义的经典著作,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著《伟大种族的消逝》(The Passingof the Great Race)在美国出版,同样以戈宾诺理论为基础。
然而,戈宾诺的理论虽然宏大,却不精致,只有定性的推断而没有定量的证明,“科学性”不高;而且,他更关心的是对历史的解释,而不是要拯救人类的未来。打着科学的幌子推销种族主义和等级主义,以及设计具体的方案防止人类的退化,这两个任务留给了伪优生学的创建者、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在1869年出版的《遗传的天赋》(Hereditary Genius)一书,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高尔顿的伪优生学建立在“逻辑推理”和“统计”基础之上。其“逻辑推理”并不新鲜,也就是退化律,即如果不加以人工干预,人类的遗传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一步步退化。这根据的是当时流行的“融合遗传”的错误概念,把人类的遗传,当成就像是从男、女双方各取半杯水混和成一杯水,这样一代又一代地混和下去,原先“优良”的水当然也就一代又一代地被被稀释掉了。高尔顿所说的遗传,并不只是体质,而是认为人类一切特征,特别是智力、品质、道德、创造力等等,也都是能遗传的,心灵方面的遗传其实才是他更关心的。这种信仰也是由来已久,高尔顿的独创之处,是采用了统计的方法定量地加以证明。例如,他统计了从1660年到1865年间286位著名的英国法官,发现九分之一有父子或兄弟关系。于是他得出结论说,当法官的能力是遗传的,这些法官天生就继承了当法官必备的品质。显然,高尔顿犯了统计上的两大错误,一是取样不随机,二是缺乏对照,完全无视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家庭环境对职业取向的影响、裙带关系对升迁的影响等等)。他用同样的方法证明了科学家、诗人、政治家、将军甚至划船手等等全都是遗传的。这个结论尽管在今天看来非常荒唐,在当时却深受欧洲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的欢迎,迎合了他们觉得自己天生就高人一等的心态。高尔顿是一位等级主义者,认为下等人之所以是下等人,是因为他们天生在智力、体力和道德方面就下等。他的统计已“证明”了这一点。他更是一位种族主义者,在他看来,并被他的研究所“证明”,北欧人无疑是最高等的人种,而黑人有着最低等的人种,最低等的种族的智力甚至还不如聪明的狗:
“尼格罗种族(黑人)的平均智力水平,要比我们的低两等。”
“雅典种族的平均能力,按最可能低的估计,也几乎要比我们高两等,也就是说,与我们的种族高出非洲尼格罗种族的相当。”
从古代雅典人到当时的欧洲人,已经退化了两等,而他所担心的,是欧洲人所保留着的那些“高贵品质”,包括发达的智力、强健的体力、高尚的道德、深刻的洞察力等等,正在很快被高出生率的贫苦欧洲人和非白种人所稀释、败坏。为了将人类从灾难的边缘拯救下来,高尔顿从动植物育种(也就是他的表哥达尔文所说的人工选择)得到启发,提出了两套方案(这两套方案被其追随者称为“积极优生”和“消极优生”),一方面,“上等人”只能跟“上等人”结婚,并且要尽可能多地生孩子,他写道:“如果那些最适宜占居大地的种族被鼓励早婚,在几代之后,他们将会取代了其他种族。”另一方面,高尔顿呼吁政府插手,劝阻或防止“下等人”生殖。他相信,其结果将会是非常成功的:
“在家养动物以及进化历史上,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怀疑,(通过优生学)将会形成一个心智健全的种族,他们在心智和道德上比现代欧洲人高等的程度,与现代欧洲人比黑人中最低等的种族的高等程度相当。”
他希望伪优生学能变成一种世俗宗教,让“下等人”出于宗教的狂热,为了人类的未来而自觉牺牲自己的生殖权利,而让“上等”的欧洲人大量繁衍,这会使得全人类的品质大为提高,进而进化出更高级的人类。这应该成为人类的最高道德召唤。
在世界各地(欧洲各国、苏联、美国、巴西、中国、日本等),在各行各业的人士(科学家、医生、社会活动家、女性主义者等等),高尔顿都很快找到了大量热心的追随者。1895年首先从德国开始,高尔顿的福音被称之为“种族卫生”。1912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吸引了世界各国的750名参加者,来宾中包括邱吉尔和贝尔。在1890-1930年间,有大约30个全国性的优生学学会在世界各国成立。优生学在名牌大学被传授,在标准生物学教科书被介绍。不过,世界各国对优生学的热衷和推广程度并不相同。例如在法国,优生学活动家们强调对孕妇进行教育,鼓励多生优育,但是排斥进行婚前诊断和强制绝育,并未真正采用高尔顿的方案。在英国,情况与此类似。高尔顿的优生方案首先在美国得到实施,之后在德国被推向了极端。
高尔顿的逻辑推理,建立在对遗传机制的无知之上。在20世纪初,孟德尔遗传定律被重新发现并很快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孟德尔遗传定律证明了遗传并不是融合的,推翻了高尔顿的退化律。但是高尔顿的优生方案并没有随之被推翻。恰恰相反,早期的遗传学家相信孟德尔遗传定律为优生学提供了更为牢固的基础。他们不仅认为人的一切特征都能遗传,而且都遵循孟德尔遗传定律,以颗粒的形式固定地永久遗传下去,因此,用人工干预的办法消灭劣质性状,就更为迫切了。他们最关心的劣质性状是所谓“低能”,这指的是一切心灵缺陷,不只是智力缺陷,更包括心理、行为缺陷,它被认为是导致贫困、犯罪、道德败坏等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因素,是与生俱来、无法通过教育和环境加以改变的天性,而且是可遗传的单一性状。1921年,美国遗传学家达文波特(Charles B. Davenport)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的一段话,表达了当时遗传学家的普遍意见:
“通过对家族史的广泛深入的分析,似乎非常可能地,中度和高度的低能是做为一个简单的隐性性状遗传的,或者大约如此。据此可知两个低能的父母应该只有低能的儿女,而这正是实际所发现的。”
果真如此的话,要解决社会问题,就有了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通过优生消灭这一导致低能的基因。早在1911年,达文波特在《与优生学有关的遗传》一书中,就已为美国优生学运动制定了行动指南,而这不过是高尔顿两套方案的改头换面:
“优生学者的普遍方案是非常清楚的——即通过引导年轻人对配偶做更合理的选择,理智地恋爱,而改进人种。它也包括由政府控制心灵不健全者的繁衍。它并不暗示在出生前或出生后消灭不适者。”
直到1925年,摩尔根才成为遗传学家中第一个公开地质疑优生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案。但是当时美国遗传学界的主流仍然支持优生学运动。在1928年国际遗传学大会指导委员会任职的100名美国遗传学家中,有42人是优生学运动的活跃分子,剩下的人要么消极地支持,要么保持沉默,敢于公开批评优生学运动的遗传学家很少,尽管这时候,已有许多证据表明,人的智力、心理、行为并不是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更不是由单一基因决定的,而是由多个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与高尔顿一脉相承,美国优生学家既是等级主义者,也是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优生学运动能在美国风起云涌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来自西欧、北欧的旧移民对来自东欧、南欧的新移民的种族歧视。印第安那大学细菌学家莱斯(ThurmanRice)在1929年出版的《种族卫生》(Racial Hygiene)一书中,即如此声称:
“我们以前所接受的移民实际上都来自北欧。他们大多有优良的品质并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今天的情况非常不同;目前,或至少是现有法律通过之前,到来的新移民大多数来自东欧和南欧,或者来其他更无关联的地区;他们与‘熔炉’中我们的血缘不相混合,如果相互杂交的话,他们的显性性状将会盖过我们原有的隐形性状;他们通常是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引起无穷无尽的麻烦;他们有非常低的生活水准;他们扰乱了今天的劳动问题;他们极其多育。”
莱斯说的“现有法律”,指的是美国国会在1921年和1924年通过的限制中欧、南欧和东欧移民的法案,法案被提出和通过的一大理由,就是那里的人民属于低等的种族(由“智商测定”所证明)并倾向于生育有缺陷的子女,几名优生学家为此到国会作证。
达文波特为优生学运动制定的两个普遍方案,第一个根本无法实施:众所周知,爱情是盲目的,又如何能使年轻人“理智地恋爱”?达文波特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无法说服。因此美国优生学运动的主要手段,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府干预,进行“消极优生”。到20年代,美国优生学家们已成功地游说几十个州的议会通过了对社会不适者强制进行绝育的法案。这些不幸者中排第一位的是“低能”者,还包括疯子、犯罪分子、病人(包括肺结核、梅毒、麻疯病和其他慢性传染病患者)、盲人、聋子、残废,以及孤儿、无家可归者、流浪汉等一切带来社会负担的人。到1935年,有28个州通过法律对孤儿院的孤儿、精神病院的病人和监狱的犯人强行实施绝育手术。光是加利福尼亚一州,就将12941人强行送上了绝育手术台。美国优生学家或许会争辩说,他们很“人道”,只是对不适者进行了绝育,并没有“在出生前或出生后消灭不适者”。但是,既然认定了某个类群的人天生就低人一等,这些人即使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也依然是一大社会负担,那么从经济的角度看,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要合算得多,所需要的,只是撕下“人道”的遮羞布。而这,正是稍后在德国发生的情形。
1923年,三位德国著名生物学家鲍尔(Erwin Baur)、费希尔(EugenFischer)和冷兹(Fritz Lenz)合作出版了一本教科书《人类遗传和种族卫生原理》,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赞扬,成为欧洲和美国大学遗传学的标准教科书。这本教科书详细介绍了人种学和优生学的基本原理,目的非常明确:“如果我们继续浪费我们先天的心理遗产,还像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那样浪费,那么要不了许多代,我们就会不再比蒙古人更优等。我们的人种学研究不能导致傲慢,而必须导致行动——导致优生。”当20年代初希特勒因啤酒店政变失败坐牢,在监狱中撰写《我的奋斗》时,这本教科书是他的科学参考书。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计算出要经过600年有系统的绝育,才能使人类恢复健康,不过对一个将要持续千年的帝国,这么做还是值得的。1933年7月14日,新成立的第三帝国通过了“防止遗传病后代法”,对精神分裂患者、抑郁症患者、低能者、癫痫病患者、酗酒者、先天盲人和聋子以及舞蹈病患者强行绝育。在以后的三、四年间,多达40万人被“遗传健康法庭”判决实施绝育。到1934年,有色人种的小孩都必须被绝育。之后被送上手术台的是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有关个体”。这时候的纳粹德国还可说只是在步美国优生学运动的后尘,纳粹公开声称加州等地的优生立法是他们的榜样,而访问德国的美国优生学活动家也纷纷写报告赞扬德国的优生学运动。至迟到1938年,德国的“种族卫生”运动就有了质的飞跃:种族卫生主义者声称,不应该让那些有先天缺陷或患了不治之症的人继续在人间受折磨。这些人生不如死。于是“安乐死”取代了绝育手术。1939年9月1日,在入侵波兰的同一天,希特勒在一封信中指示由特定的医生对病人进行评估,对那些无法治愈者实行“仁慈的杀死”。数十名医学和精神病学教授奉命对283000名病人进行评估,75000人被判决饿死或注射毒药杀死。精神病患者如果生病,则不予治疗,任其死亡。在1940年10-12月间,波兰的4400名精神病患者和德国的2000名精神病患者被枪杀。一些医院开始试验效率更高的屠杀方式:使用毒气。到1941年,已有70723名精神病患者被用一氧化碳毒死。比起“最后解决”,这些不过是小小的试验而已。最后被“解决”掉的,包括五百多万犹太人和难以数计的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精神病人以及其他危害“种族卫生”的人士。
在这场大屠杀中,德国科学家们密切配合。德国人类学、生物学和医学等学术领域根据种族主义和优生学的原则进行“改革”,研究人员积极参与鉴定、绝育和灭绝那些“不卫生”者的活动。《人类遗传和种族卫生原理》的三位作者中,鲍尔死于1933年,无缘见到理想的实现。冷兹在1937年加入纳粹并成为威廉大帝人类学学院的系主任。费希尔在1940年加入纳粹,并成为该学院的院长。在1943年,费希尔宣布:“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勇于迈出开创性、决定性的第一步,为了德国人民在德国人民之中取得如此辉煌的种族卫生成就,他们的不朽历史功勋,将永被铭记。”纳粹的副领袖赫斯则声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过是“应用人种学”。
1939-40年的冬天,一位名叫埃林格(Tage Ellinger)的美国遗传学家访问德国,在威廉大帝人类学研究院与费希尔会面。在1942年的《遗传学杂志》(Journal of Heredity)上,埃林格报告了他的访德观感》。他一方面谴责纳粹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属于“人类兽性的可耻范畴”,另一方面则声称纳粹德国的优生计划的本质并不可恶,并对“甚至连纳粹也能从生物科学得到帮助”感到沾沾自喜。埃林格的“一分为二”观点在当时的美国生物学界很具有代表性。甚至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坚持认为,优生学的宗旨是好的,只不过在历史上被种族主义者利用了。纳粹究竟是在歪曲优生学的宗旨,还是把优生学家不敢或无法实现的理想付诸现实?如果把社会经济问题归结为遗传问题,如果把遗传方法当做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捷径,那么,进入“人类兽性的可耻范畴”,其实就是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待续)